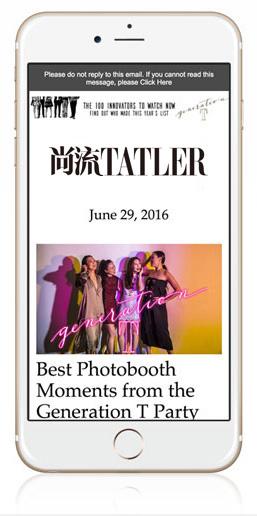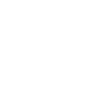如少年般上下求索
 蒋琼耳当代生活品牌“上下”首席执行官及艺术总监
蒋琼耳当代生活品牌“上下”首席执行官及艺术总监
2008年,在当代设计领域已小有名气的蒋琼耳开 始筹备自己的品牌,两年后,伴随着蒋琼耳的第一 个孩子诞生,“上下”的第一家零售店也于 2010 年 9 月开幕了。“孕育一个品牌,就像生一个孩子,从 什么都不会,到学会吃饭、说话,从爬到走,再到 学知识、做规矩......如今我的孩子 8 岁,‘上下’几 乎同龄。”
回顾创立品牌的这些年,蒋琼耳自认为做了三 件事,第一件就是建立风格。“不管你是否来自一 个大户人家、故事讲得再好、有再多人给你站台, 没有好的作品是行不通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然 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谈风格。眼下‘上下’的风格算 是有了一个雏形,让人一看我们的作品就知道这是‘上下’。但因为品类繁多,想要在调性风格上做到 高度统一是很大的挑战。”
蒋琼耳清晰地记得品牌刚起步时爱马仕全球艺 术总监 Pierre-Alexis Dumas 对她说的话——“做‘上 下’的艺术总监,比做爱马仕艺术总监还难,因为 爱马仕的风格已经传到第六代了,经历了百年的考 验,如今需要做的是传承与发扬,但‘上下’要从零 开始。”在蒋琼耳看来,当时的她就像在茫茫大海中 飘荡,360 度什么方向都可以去,但又不是想去什 么地方就能去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探索, 一边调整方向。
“我觉得就像一个家庭,只要核心 的价值观不变,即便时光变迁, 终将随着历史的长河而留存下来;在滚滚浪涛中,仿佛一块大的 盘石,不会被冲走;或者说是一棵 大树的树根,扎得越深,再大的风暴也不会将树吹倒。”
让蒋琼耳自豪的是,这几年她以“上下”为中 心,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基础的手工艺产业链。“我 们都知道,欧洲的高端品牌都有一个完整的手工艺 产业链在支撑,但中国没有,往往是孤零零的一个 作坊,几个老师傅带几个徒弟,整体而言缺乏管理。 当我们设计出一件产品,比如今年秋冬我非常喜欢 的一副旅行跳棋,需要用不同的工艺和方法把红眼 石、白玛瑙、红玛瑙、紫檀和竹木结合在一起。”
其实最早在样品研发阶段,蒋琼耳的团队跟手 工艺老师傅合作得挺好的,可一旦产量上去了就会 脱节、掉链子,次品率很高。“手工艺品当然不比机 器开模制造的东西,可以允许一点偏差,但必须要 有一个标准,否则我自己这关都过不去。于是研发 周期从最初计划的半年,到最后花了两年半,攻克 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在这过程中,我们也从源头 开始着手系统地管理各家手工作坊。今天会有一些 老师傅跟我说,当初觉得你们提的要求太离谱,但 最后真的做到了,觉得很自豪、很满足。近来又有 不少年轻人加入,通过培训,成为新一代的手艺人。”
除了产业链,蒋琼耳也在努力建立品牌的价值 观。“我觉得就像一个家庭,只要核心的价值观不 变,即便时光变迁,终将随着历史的长河而留存下 来;在滚滚浪涛中,仿佛一块大的盘石,不会被冲走; 或者说是一棵大树的树根,扎得越深,再大的风暴 也不会将树吹倒。每当我在面对品质、价格和时间 之间的矛盾时,我不愿意放手的一定是品质。”
“上下”初创时发布的大天地家具系列、羊绒毡 子系列服饰、竹丝缂丝的茶具,已经成为品牌的经 典,而今年推出的海魂衫揽月包和形似月饼的糖果 包,也将带着蒋琼耳的童年记忆,加入“上下”明星 产品的阵营。“我的设计原则是,取之神,弃之形。 今年的年题是‘少年行’,但我不会把年少时的红领 巾、黑板报放到设计里面,我需要放掉这些‘形’, 而去抓住时代的神韵。我希望用这些年积累的点点 滴滴的情感,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怀着好奇心讲故事
 陆川 电影导演
陆川 电影导演
提到导演陆川,我们脑海中会出现他的《寻枪》《南 京!南京!》或是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而这 些电影镜头里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蛮荒”。
“早期的《寻枪》《可可西里》这些作品中的西部蛮荒 元素,可能给大家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大家看惯了 我以往的电影,会觉得我比较偏爱那种纪实风格或 者是比较质朴的画面。但其实我每一次创作都会有 新的变化,像战争片《南京!南京!》、历史片《王 的盛宴》、科幻探险片《九层妖塔》、自然电影《我 们诞生在中国》,在类型和题材上非常多元。我并 不排斥那种很时尚和流行的拍摄风格,用什么手法 其实是要根据拍摄对象来定的。”
在陆川看来,电影的灵魂一定是故事,只有故事才能打动观众,导演的工作是要用好的拍摄手法和角度去讲好这个故事,而演员是要通过好的表演展现出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和情感望。“好导演和好演员、好摄影等等都是电影的加分项,但是归根结底观众看的还是一个好故事。首先肯定是要打动人。
他很欣慰地看到现在国内的电影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也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但同时认为,我们的电影工业与好莱坞还存在 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影片的国际化制作,全球 化发行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电影就谈不上走出国门和文化输出,更别提打 造一个全球化的电影市场。”
说到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的权衡,陆川认为艺 术性和商业性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因素。“电影 从诞生开始就有商业属性,而且随着电影的投资越 来越大,它的商业属性也会越来越重要。但并不是 说艺术性就不重要了,正因为有了艺术性,电影才 能创造出更具魅力的动人故事,才能让电影更有商 业价值。我们真正应该反对的应该是那种唯票房论, 较完善的电影工业化制作流程。”
不是说一部影片不赚多少个亿就不能见人了,相反 还要考虑一部影片的艺术价值对于大众和社会起到 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方面其实像《摔跤吧!爸爸》 这类电影其实都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对陆川而言,在如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能 丢失的就是好奇心。从陆川过往的作品中不难发现, 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导演,从故事片到科幻片, 从现代题材到历史题材,从拍人到拍动物,是好奇 心让他不断去探寻和了解这个世界,保持旺盛的精 力去不断学习,创作出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新作品, 拥有一颗好奇心也是陆川的生活态度。
最近翻开陆川的微博,除了与电影相关的内容 之余,多是儿子葫芦的生活照片和短视频,甚至还 会和网友互动,交流育儿趣事。今年 6 月是他和太 太胡蝶结婚三周年的纪念,他在微博上感慨说 :“三 周年,我在上海忙工作,你在北京录节目。没能在 一起庆祝,特别遗憾。想对你说:葫芦妈,都在心里, 都记着,恍若昨日。”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一些经典作品,都是以人类共通情感为核心,有可能它记录的时代背景与现在 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人类情感却是始终不变的, 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作品的,一定在情感上能够给几 代人持续的感动。”
越来越忙碌的陆川眼下正筹备准备开拍《749 局》,一部与《泰坦尼克》有些类似的灾难爱情电影。 “这部电影已经筹备了两年时间,我们也邀请到了 多个国家的制作团队共同参与制作,希望通过这部 电影积累更多电影的国际化制作经验,创建一个比较完善的电影工业化制作流程。”
天地有大美
 蒋勋 画家、诗人与作家
蒋勋 画家、诗人与作家
蒋勋出生于西安,童年则在台北大龙峒度过,当时很多家庭没有空调、电视和电话,连广播都很少, 可蒋勋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个会讲故事的 母亲。“我妈妈总是诱惑我跟她一起做家务,而诱 惑的方法就是一边做一边讲故事,她的口才绝对比 我好 10 倍以上。 那时的夏天很热, 她常常在我们 家门口讲白蛇传,然后一条街的小孩都在我们家口 听,而且听完还觉得不够,妈妈说太晚了,明天再来, 于是第二天他们就又搬着板凳在那里等。‘松下问 童子,言师采药去’之类的唐诗宋词,我不是读来的, 是听来的。”
在蒋勋的记忆中,是母亲的言传身教让他自然 而然地学会在生活中向往美,这种美可能来自一首 诗,也可能是想象一条白蛇如何变成一个女人,去 寻找她爱的对象。“长大后,我在大学里教书,我 发现自己不太喜欢大学的教育。我们在课堂里讲美 学,通常是讲黑格尔说了什么、得出什么结论,我 觉得其中有一部分是跟生活完全脱节了。”
2014 年,蒋勋到台东池上做驻村艺术家,原因 是他一直在都市里找不到心灵的故乡。“我想,人 的一生中会有好几个心灵的故乡,不一定是你出生 的地方,比如前两个月我回到巴黎,就感觉回到了 25 岁的学生时代,穿一条破破的牛仔裤,买一瓶红 酒在塞纳河旁边读泰戈尔的诗。这些年,我认识了 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可我很少去池上。我觉 得那里好远,甚至比纽约还远,其实只要坐 3 个小 时的火车就到了。所谓远,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 是心理上的。我发现我对土地的了解非常少,于是 就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功课,去池上,认识土地和农 民,在都市人已经忘却的日出日落、晨昏循环里, 寻找自然秩序,分享土地。”
在驻村的日子里,蒋勋找回了黎明时的喜悦、 黄昏时淡淡的感伤、春天的狂喜、秋天的落寞与孤独。“其实人的身体里有四季,我们也需要休息,最美 好的生命应该是处于自然的状态,有日出就有日落, 有蓬勃的生长,也要休养生息。”作为生活在都市里 的知识分子,蒋勋觉得自己有时候已经忘掉分享是 怎么一回事,“有一天,我发现门口放了一堆丝瓜和油菜花,我以为是谁拿不动了放在我门口,就到处 问邻居们,但没人理我,直到后来有一个老太太跟 我说,你们台北人很奇怪,我们家里蔬菜多了就会 放在邻居家门口,有什么好问的......她的话让我觉 得好惭愧,是我忘了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别 人分享。在农村里,大家一起劳动,下田割稻,分 享劳作的成果。我觉得自己这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所 谓上等人,其实不如农民。所以我很高兴到这个年 龄有了新的老师——张天助、梁正贤等等,他们没 受过很高的教育,可是他们教会我去尊敬土地、生命和他人。”
今年初夏,蒋勋在佳士得上海艺术空间举办了 一场名为“天地有大美”的展览,对于这句摘自《庄 子》中的话,蒋勋有他自己的解读:“所谓‘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是告诉我们,天地自然中无所不在 都是美,我们身处人类社会,习惯于排名和区分—— 因为这是美,所以那个就是丑——可是在自然中我 们很难说什么东西是丑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欣赏每 一种生命的现象。”
在蒋勋看来,美是回来做自己。“做自己其实 是最难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人,觉得很美,就照 着样子穿衣打扮,很可能不是变成美,而是变丑了, 因为每一个生命有它自己发展的过程,有它自己完 成自己的方式。一个充分自信的生命才敢说——我 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自己,我没有伪装,也没有 委屈自己。它跟我们世俗上所谓的美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我不是让大家爱艺术,而是应该爱自己,我也 希望用这样的东西来提醒自己,如果爱美、爱艺术, 不要在美和艺术里,伤害任何的生命。”
以音乐治愈世界
 吕秀龄 上海交响乐团国际顾问理事会副主席
吕秀龄 上海交响乐团国际顾问理事会副主席
吕秀龄这个名字,已经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很长一 段时间。1981 年,在电视节目里演奏琵琶的吕秀龄 因气质独特而被琼瑶看中,出道的第一部电影就演 了女一号,此后她在20多部电影中担任主角,和 同一班人马合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像是“在一个 大家庭里,被大家保护和照顾”。正因为如此,她 自认为与演艺圈几乎绝缘。
1 9 9 4 年 , 吕 秀 龄 因《 云 南 的 故 事 》被 上 海 电 影 评论家协会评为最佳女演员,也是在这一年,她结 识了投资银行家 Ivan Cheah,三年后与他走进婚姻 的殿堂,并跟随他去伦敦工作和生活,后又搬到纽 约。11 年前,他们定居上海,从此成为上海交响乐 团忠实的支持者,并与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和团长周 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不管在什么城市,我们都去听音乐会,我觉 得音乐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不论是认识新朋 友,还是在一座新的城市去了解当地的文化,产生 共鸣。当我看到不同国籍的演奏家,在舞台上诠释 一个曲目, 真的很感动。 我们结婚 21 年了, 每每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我们就会说‘play some music!’我先生毕业于朱利安音乐学院,学的是小 提琴,尽管如今从事金融行业,但我们对音乐的支 持多年来从未改变。能在上海听到这么多国际知名 的音乐家演奏,真的很有耳福和眼福。”
2018 年初,吕秀龄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团国际顾 问委员会(IAB),目的在于提升中国一流文化机构 的国际形象和知名度,19 位成员来自世界各地,都 是音乐爱好者。说起来,吕秀龄与音乐的缘分始于 6 岁,她在当时以音乐教育出名的台北天主教光仁 学校学钢琴,10 岁时机缘巧合开始学琵琶,两年之 后在全省音乐比赛中作为少年组年纪最小的参赛者 获得了一等奖。
“我觉得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启蒙老师,叫 王正平。前两年他在台北过世,我去参加了他的纪 念音乐会。琵琶算是中国传统乐器里我觉得最难的 一个,所以我也蛮骄傲的。这些年来,不管是演奏 音乐还是欣赏音乐,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治
疗和洗礼,尤其是在这个忙碌和焦虑的时代,音乐 让人愉悦与平静。所以我希望在得到这么多之后, 回馈一些什么。”因为吕秀龄夫妇的积极牵线,纽约 爱乐乐团近些年与上交互动频繁,已连续四年为上 海夏季音乐节举办开幕音乐会。
提到两年前开幕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吕秀 龄掩不住的自豪。“为了避免附近地铁对于音乐厅音 响效果的影响,整个建筑浮筑在 300 个弹簧上,是 国内第一个请音效设计师与建筑师合作设计的音乐 厅。如果是在这里办独奏音乐会的话,水平必须非 常高,因为一点点瑕疵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真的是 一个高难度的舞台。”吕秀龄谈及上交的音乐家们, 更是连声赞叹,“我们乐团的平均年龄可能都不到 40 岁,远低于国外的一些老牌乐团,但水平绝对不 输他们。”
小提琴家李沛加入上交已有 9 年,目前担任乐 团首席,他说,明年就是上交 140 周年,眼下大家 正抓紧排练,与德国著名厂牌 Deutche Gramophon 合 作 录 制 乐 团 近 1 0 年 来 的 首 张 唱 片 :“ 吕 秀 龄 老 师 给我的印象是美而且亲切,她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 听众。”上交大提琴副首席朱琳也表示:“两年前我在 吕秀龄老师组织的一场音乐家的聚会上认识了她, 我觉得她为古典音乐和我们乐团带来了更多来自社 会各界的关注,对此我们是很感激的。”对于音乐家 们 的 认 可 , 吕 秀 龄 谦 虚 地 说 :“ 我 本 身 就 很 喜 欢 和 音乐家们交往,他们在台上充满魅力,在台下却是 羞涩而单纯的,和他们交流让我很受用。我特别期 待明年上交的全球巡演,希望看到这张上海的城市 名片被更多国际的观众熟知。”
“这些年来,不管是演奏音乐 还是欣赏音乐,我觉得音乐 对我来说是一种治疗和洗礼, 尤其是在这个忙碌和焦虑的 时代,音乐让人愉悦与平静。”
打捞时光的遗迹
 尔冬强 视觉文献开创者
尔冬强 视觉文献开创者
从绍兴路上的汉源书店到陕西南路上的汉源汇,尔冬强与书结缘已经22年了。离开媒体后,尔冬强成为中国内地最早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摄影家,拍摄了大量印证近代上海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老建筑,比如教堂和教会学校,也着手研究了中国近代通商 口岸及海关史、邮政史、银行史等等,在国内开启“视 觉文献”的先河。说起来,尔冬强最初想到开书店, 是因为找不到地方售卖自己在香港出版的摄影集。
“20 多年前, 我在香港创办了中国通出版社, 我的《最后一瞥——上海西洋建筑》第一版印了五千 本,三个月就卖完了,因为当时在香港半山住了很 多上海人,他们1949年之前离开故乡,之后就没 回来过,看到我拍的那些陪伴他们出生成长的街区 和房子,对他们来讲是很感动的。后来我选择开一 间自己的书店,除了卖自己出版的进口书,也是想 要有个看书、喝咖啡、谈话的空间,这样的书店我 在环球旅行时见过不少,但当时在国内还是比较少 的。”
一间小小的书店或许不太起眼,但20多年下 来积攒的故事,尔冬强可能说个几天几夜也说不 完。“书店附近有一家私立学校永昌小学,学生们 放学后会来书店补习功课,长大以后有人回到这家 书店拍结婚照,甚至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书。一 家书店开得久了,承载的也许是一代人甚至两代 人的记忆。”
在书店的老客人里,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张 国荣,他每次来都会待上一整个下午。“因为他的 工作比较繁忙,又不太喜欢热闹,有这样一个安静 的空间暂时休息一下,他可能觉得很舒服。我在店 里放的基本上都是老旧的东西,可能跟他的审美趣 味比较接近吧,后来他在门口拍了一张很有意思的 照片,背景就是我的一辆老吉普车。那辆车现在已 经很破旧了,但我还把它留在郊区的房子里,算是 纪念。汉源书店关掉后,我把门面整体拆下来移到 仓库里,以后要是有机会做回顾展,我没准可以把它重新搭起来,还把那辆汽车停在门口,把在这个书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再好好梳理一回。”
这些年,尔冬强走南闯北,去了很多地方,他驾驶吉普车和帆船,身体力行地重走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我是一个用时代来思考人生的人,如果 要制定计划,通常一定就是10年、15年。1999年, 我跟媒体说,打算花 15 年做一个题目,就是重走丝 绸之路,一眨眼已经 19 年了,还没做完,因为这个 题目实在是太大了,需要读的书很多,而我又不是 一个仅仅读书就行的人,当我在书里读到一个地方, 产生兴趣,就要到实地去采访,于是这个过程就变 得比较漫长。”
6 年前自从开始学习驾驶帆船,尔冬强便有机 会从海上去打量一座城市。 每到一座港口, 他会 先去看灯塔。“我印象最深的一座灯塔在巴达维亚, 历史非常悠久,在上面能够俯瞰巨大的胡椒贸易港, 商船来来往往,都靠它指引航向,历史上有很多文 人曾和我一样在这个灯塔上凭栏远眺,比如康拉德、 毛姆和高罗佩。”其实南洋很多地方,比如菲律宾群 岛、马来西亚群岛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港口城市, 都能看到大量中国文化的遗存,不管是民间信仰的 庙宇,还是迁徙过去的华人家族留下来的祠堂与大 宅,大量的文本与实物在坊间流传,他的工作就是 收集和梳理这些历史的档案。尔冬强曾在中华艺术 宫 6,000 平方米的空间办过《一个人的丝路》视觉文 献展,他希望将来能有 1 万平方米的空间,去展示 他重走丝绸之路沿途找到的文物和摄影作品,甚至 可能在一个类似剧院的空间,通过屏幕和舞台呈现 这些内容。每一次旅程归来,汉源汇作为一间客 厅,成为他与朋友们谈论所见所闻的据点,而他也 在这里举办了不少座谈和展览。“如今很多政府机 构、上市公司都蜂拥开起书店或类似于书店的文创 空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可能还是 需要时间来检验,未来能否允许更多的独立书店生 存还是未知数。”
完美是流动的
 徐冰 艺术家
徐冰 艺术家
前不久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有一场 名为“徐冰:思想与方法”(Thought and Method) 的展览,在业界引起诸多讨论。1980 年代,徐冰作 为中国先锋派的成员之一,其概念与装置艺术融合 了视觉文化、媒体技术与语言交流,享誉国际。如今, 他与劳力士达成合作关系,担任劳力士创艺推荐资 助 计 划(Rolex Mentor and Protégé Arts Initiative) 的顾问,而本次展览正是徐冰至今在北京举办的展 览中最为全面的回顾展,其中包括他颇具话题性的 作品“天书”。
“完美是流动的,没有绝对的完美。 谢德庆先生是个有艺术洁癖的人,他跟我说,‘天书’不能再展览了,因为在 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已经是最好的形式, 如果再有第二个形式就说明两个都不好。”
徐冰坦言,做“天书”时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只是一心想做和国际艺术接轨的当代艺术,但不懂 当代艺术是什么。“我想从旧的艺术中出来,所以 最后在‘出不来’和‘进不去’的夹缝中硬是去做自己 认为的当代艺术。从方法到材料、沟通方法全是中 国的古代哲学智慧的内容。”刻字的时候,徐冰想到 要做什么会感到兴奋,但第二天就会觉得自己很傻。 有的想法,即便一两年之后仍然会想到它,并带来 新的补充,这时候他才会认为这个想法值得全力以 赴去做,把它推进到极致。“文字有尊严,来自于 不能被世俗滥用。外包装部分代表了文化的尊严和 内涵,就像书法一样。一首诗挂在家里,诗的内容 已不重要。中国书法了不得就在于把文字的外包装 推进到极致精美的程度。”通过近日这场回顾性的展 览,徐冰看到了自己的样子,怎么工作、怎么思考,
“一个艺术家最终是一个闭合的圆,这个圆就是艺 术家自己。因为只要是你真诚的作品,哪怕是新的 作品,都能揭示出已经存在的东西。”
徐冰发现,每次呈现由于环境的限制,确实 让呈现无法达到自己所认为的完美。“完美是流动
的,没有绝对的完美。谢德庆先生是个有艺术洁癖 的人,他跟我说,‘天书’不能再展览了,因为在中 国美术馆的展览已经是最好的形式,如果再有第二 个形式就说明两个都不好。我之前很信这个,后来 就不信了。我觉得所谓的好坏也是流动的,任何事 情都应该在关系的流动和变异中去判断。比如,我 现在决定这样做最好,但观众进来后,环境和关系 就变了。我在美术馆使用一些空间,我发现有些不 好用的空间有时候我到很喜欢,因为这种不好用就 把你逼到死角,让你调动作用的思考力让作品起死 回生,想到你过去没能想到的内容。如果里面掺杂 虚假的内容,虽然省了事,但毫无意义。”徐冰告诉《尚流TATLER》,他的艺术启蒙发生在幼儿园。“每 一个孩子都曾经喜欢过画画,有些孩子发展了这个 兴趣、有些孩子发展了其他方面,我就属于继续画 画的那种孩子。我的艺术生涯不是计划和预期所得, 它是宿命的。”
在徐冰看来,艺术家必须是有思想的,但这个 思想必须是通过工作、艺术方法来表达出来。如果 没能完成这个工作,就不能算一个称职的艺术家。 所有的艺术史,都是记载的对艺术语言有所推进的 人。没有工作,一切的思想都是无效的。根据徐冰 的实践体会,“推进”来自系统之外,如果在系统之 内,其实谈不上“推进”,要补充新的东西一定是系 统或者自己认知之外的内容。一旦把这个内容带入, 才有“推进”的方向。如果只想着艺术的推进,一定 推进不了。任何领域真正前沿的东西都在领域的边 缘地带,或者与其他领域重叠处,或直接在这个领 域之外。
从根本上而言,徐冰对艺术能从多大程度上解 决社会问题持怀疑态度——在当今社会,艺术究竟 怎样起作用?“一幅画挂在家里赏心悦目,有种符 号化的认识。对于我来讲,艺术的价值在于通过我 的作品,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路数,这种 东西通过我的无法归类的作品起作用。”由批评家从 艺术家的生活中提取的蛛丝马迹,最后提出新的概 念和知识,徐冰把这种概念跟新到艺术史之中,给 人类社会带来贡献。人类永远会碰到与知识、阅读 间的关系,如果徐冰的作品能给出一种参照,这就 是他作品的价值。